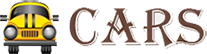前言:“‘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1]拍照片是诸多讲述灾难的行为的一种。历史告诉我们,游走在灾难现场的持相机的人不一定是专业人士,他们可能只是平民。
如今,持相机的人正在用手机拍照、发社交媒体等方式见证着灾难。和诸如约瑟夫·寇德卡、詹姆斯·纳切威、苏珊·梅塞拉斯等长期工作在灾难第一线的专业摄影师相比,他们更像是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特殊年代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中的特蕾莎。冲突。牺牲。见证。谎言。审查。严肃中点缀着浪漫,历史的视野中缠绕着对自我的理解。关乎生命的灵与肉、轻与重,时而能承受,时而不能承受。
1968年,捷克人寇德卡来到布拉格。与他一同前往的除了一支25mm超广角镜头,还有他那极致的眼光、无可匹敌的勇气和完美主义。这位神秘而固执摄影师留下了海量的照片,由此成为“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见证人之一。
“见证人”是人们在谈论诸如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灾难时常常提到的词。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所见证的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摄影师寇德卡、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电影《布拉格之恋》[3]中的主角特蕾莎与托马斯,所见证的则是1968年俄国铁拳下的布拉格。
寇德卡所见证的布拉格包含了诸多街景:尽管伴随着焚烧汽车、“占领”坦克、旗帜飘飘,照片中布拉格的街道依然宁静得令人生疑。楼房,马路,树。偶见的废墟里不乏萧索,但总体上仍秩序井然。我一张张地翻看,的确如此:抗议是激烈的,街道是宁谧的。这种无声的矛盾令我困惑,以至很难从中揣度出布拉格人彼时的生活状态。我试图折返到细节里,寻找人们表情里的警惕、笑脸和疲惫——他们是如何与坦克的轰鸣相处着,度过每一天?
影片的女主角特蕾莎也是一名摄影师(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她曾从爱人托马斯的公寓负气而逃,却被迫近的装甲车带来的巨大震动推回到托马斯的怀抱。在各种意义上的暗影中,特蕾莎见证了外来者可憎的脸。想必这就是她决定拿起相机、走上街头的时刻。而藏身于寇德卡实拍的照片背后的布拉格生活,正是通过虚构的特蕾莎,被电影中的照相机记录在案。
乡村女孩特蕾莎,在脑科医生托马斯的一次出诊中与他相遇。对于他沾花惹草的习性,特蕾莎一无所知。因为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特蕾莎只身一人出现在他布拉格公寓的门口,而托马斯则在意识到自己将要破戒让女人住在家里之前,就命运般地选择了与她牵手共枕。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当托马斯把她带到自己的情人、艺术家萨宾娜那里学习摄影的时候;当托马斯与她结婚,保护她,寻找她,爱上她的时候;抑或是当托马斯为她离开,再为她回来的时候。
在工作室的会面上,萨宾娜向特蕾莎展示了法国摄影师曼·雷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了两位裸女的侧面像。迷人的高低差使得左侧女人饱满的胸脯完美嵌入了右侧女人的小腹凹陷。[4]啮合般的此消彼长,在高反差的黑白摄影里尤显神秘。萨宾娜说自己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并禁不住赞叹了曼·雷为他的爱人、同为摄影师的李·米勒拍摄的窗边裸像。“她是如此美丽。”特蕾莎当然怀疑托马斯和萨宾娜的关系,但此时此刻,她们却都被曼·雷的照片吸引,沉浸于共同的、微妙的心照不宣当中。从影片后段的情节反观,这两张照片所透露的信息——相对的裸女与拍摄所爱之人——正是关于特蕾莎和萨宾娜二人的预言。
一开始,特蕾莎和照相机并不算合拍。她摆弄相机的方式,对焦和快门的节奏,及所记录的一些平平无奇的街头瞬间……直到那夜在街角见证了俄军的入侵,特蕾莎理解了手中的照相机,也理解了自己见证人的身份。俄军与布拉格人的冲突愈演愈烈。高举相机的特蕾莎在人群中腾挪,托马斯关切眼神始终紧随左右。影片在此插入了一段历史影像和伪纪录片实拍的黑白蒙太奇:在时代的狂潮之中,在无数激动的脸庞之间,这对爱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近了。
无论是缘于对伴侣的爱之信,还是对摄影的信之爱,特蕾莎脸上的稚气逐渐转化为一抹笃定而无所畏惧的微笑。在被俄国军官的手枪指着头威胁时,特蕾莎的脸上仍挂着这抹笑。此时,她持相机的手已经端得很稳了——以不停顿的拍照(shoot)回应不道德的射击(shoot),特蕾莎按快门的手没有停下。
摄影最有力的功能之一,即见证。见证摄影师之所见(拍),也见证摄影师本人(被拍)。在布拉格的街道上,特蕾莎既是持照相机的人,同时也被其他照相机所摄。当被俄方质问是否曾把底片移交给外国记者时,纯真如她,当庭做出了坦率的承认。而紧随其后的,却是同行们一连串的否认与装傻。
照片既是布拉格人记录历史的证词,也是俄方锁定意见分子的图录。面对权力机关的按图索骥,这些人的选择虽不光彩,却情有可原。但很显然,对特蕾莎而言,这样的谎言相当于把照相机摆在一个不可能的位置——既否认了自己的在场,又确信其所见为真。她为此而痛苦。她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布拉格。
特蕾莎使用一台东德百家(Praktica)LTL照相机,常用梅耶(Meyer)29mm F2.8规格镜头。对比寇德卡的那支25mm镜头,两人视角相近,所拍的照片却迥然相异。如果说寇德卡的极致冲淡了性别,那么特蕾莎的极致就是性别本身。前者关注抗议中的人,而后者则尤其关注其中的女人。特蕾莎照片里的女性犹如漂浮在黑色死水上薄薄的花瓣,浪漫却充满挑衅。作为摄影师,特蕾莎天赋秉异。
然而,等她逃往日内瓦,当地杂志社的编辑却告诉她,这些照片虽然不错,但送来得太迟。“到处都能看到在捷克的俄国人!”言下之意是,她的照片已经过时了。特蕾莎据理力争:“可是在那里,一切都没结束!”身处于中立国那荒诞的安全里,没人听得进去。有位同行好意提点她,“看看(照片里)这些撩人的姿势!你会是个顶尖的时装摄影师。你应该找个模特,尽快准备个作品集”。
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从未发生”。知道正在代替共情,具体的灾祸被压平为抽象的照片,这几乎是摄影无可摆脱的“原罪”。照相机带给我们的真相总是有限的,无论它离现场有多么近。在日内瓦,布拉格的抗议、流血、审查好像从未发生。时尚的语法仍然能够把女人胯下有男人的场景翻译成“撩人”。对于像特蕾莎这样的见证人而言,恐怕没有比这更具毁灭性的回声了。
为了在日内瓦生存,特蕾莎尝试接受同行的建议:拍摄裸女。她再次找到萨宾娜。这场戏构成了影片最精彩的桥段之一。起初,特蕾莎丢失了以往的沉着,甚至连装胶卷的姿态都透露着紧张。
当萨宾娜从卧室的纱帘(类似反光相机里的布帘)背后缓踱而出,如舞者般迎向明亮的窗口时,她的身体,作为她整个人的隐喻,也从介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神秘存在,曝光成为纯然可见的对象。房间里安置了大量的镜子(类似暗盒里的棱镜),而两个女人在其间相互追逐、互拍裸体的过程,正如一次发生在照相机内部、朝向彼此的显影。
敏感如萨宾娜,肯定看出了特蕾莎彼时彼刻的纠结与痛苦,尽管她无疑也深爱着托马斯(大礼帽不仅是她和托马斯爱的见证,也是她和那位教授情人不爱的见证)。和特蕾莎少女般的身体相比,萨宾娜的身体宛若成熟且馥郁的蜜桃。这具令男人疯狂、女人嫉妒的身体,在这场“曝光”的仪式中,却没有释放出宣战的信号。她是以女人、而非情敌的身份阅读着特蕾莎。她的裸体对特蕾莎诉说的,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
半是邀请,半是强迫,萨宾娜提出要反拍特蕾莎。她的动作果决,有时像践踏隐私的小报记者,有时像锁定猎物的贪婪母兽。照相机一如她身体的延伸,甚至可以说,当她把赤裸的特蕾莎压进沙发的一刻,照相机一如她欲望的延伸。
“看着我,特蕾莎。”她按快门的动作既挑逗又深情。眼睛迎上了特蕾莎褪去羞怯的目光。就在这一刻,特蕾莎借由照相机看清了萨宾娜的轻,而萨宾娜则透过照相机抚摸了特蕾莎的重。看与被看、拍与被拍。向对方完全敞开自己的两个女人、一双情敌,此时的状态像极了曼·雷照片里啮合的双人舞。
整段拍摄堪比一次萨满的招魂。尾声时分,的特蕾莎斜坐在红地毯上,身下是红丝绒坐垫,姿态古典沉静,宛如油画里的宫娥。后景里,炉火烧得正旺,那亦是持照相机的萨宾娜之所在。火光是照亮(illuminating),也是启蒙(illumination)。在反复几组正反打的镜头之后,影片在她们携手共谱的平衡里结束了这场戏。
特蕾莎是个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从她身上看不到所谓的勇者事迹,照相机也不是她要誓死守护的武器。从日内瓦重返布拉格时,她不假思索就把照相机交给负责审查的边境官员,脸上没有挣扎,也没有纠结。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再度变化,特蕾莎的生活里从此没有了照相机。再后来,托马斯又回来找她,两颗心好像可以和从前一样跳在一起,又好像和以前一样难以共振。她没留下什么照片,只那次和萨宾娜互拍的照片还压在乡下小屋的抽屉里。托马斯无意间翻到,于是他一张又一张看。他没有开口,表情里也没有秘密。有照相机的日子已然远去,历史的见证、自我的见证永远留在了特蕾莎、托马斯和萨宾娜的心里。见证了什么,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徐贲,“为黑夜作见证:维塞尔和他的《夜》”,《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13页
[2]捷克斯洛伐克(1918—1992)后解体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4]这张照片的原作为横图。处在画面左侧的女性实际在上侧,下侧则是一尊躺倒的石膏半身像。
胡昊(b.1990),写作者、当代艺术与摄影研究者,现为泰康空间研究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获美学硕士学位(2017)和哲学学士学位(2013)。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